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是对上诌媚,对下欺压。但他确要装出一副正义、公允的面孔,总想以美遮丑,因此往往丑态百出,令人发笑。契诃夫为了彻底剥下他的假面具,采用对比的方法,对他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奥楚蔑洛夫对“将军”一家的谄媚和对“金饰匠”赫留金的蛮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又是通过对一条小狗的褒贬来体现的。奥楚蔑洛夫为了取悦白己的主子,竟然连利用一条狗的机会都不肯放过,足见他的灵魂是多么的龌龊。
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谈奉承、卑劣无耻;从他污秽的谩骂随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同时,作者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
奥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见风使舵,阿谀奉承是奥楚蔑洛夫的基本特征。契河夫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巧妙的用五次“变色”,无情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彻底的揭穿了奥楚蔑洛夫在庄严公职掩盖下的丑恶嘴脸: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他的谄媚权责、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当他不断的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有学者研究契河夫的书信和生平后指出:“年轻的契诃夫在沉滞的八十年代描写不知自尊的小人物时.也对他们抱着指责多于同情的态度。”赫留金和切尔维亚科夫都属于这些“小人物”。
赫留金是俄国沙皇统治下的一个小市民形象,他是小说里那“一群人”的典型代表,当狗咬人了,那一群人“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他们把生活里的琐事当作唯一的意义;当赫留金的诉讼最终被判定为失败时,他们“哈哈大笑”,毫无同情心。从本质上看,这些性格特征又是小人物在那个社会环境下追求生存的手段,是和“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变”相同的。
那“一群人”和鲁迅小说里的看客一样,蕴含了作者的无奈、悲哀、批判。所以,如果说奥楚蔑洛夫的形象是鲜明的,那么赫留金的形象则是深刻的。 在契河夫的经典短篇小说《变色龙》里,相对于奥楚蔑洛夫,叶尔德林是个次要角色,他除了端醋栗、帮警官脱大衣、穿大衣三个动作、以及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四句话外,不再有其他描写。然而正如契诃夫所说:“简练是天才的姐妹。”叶尔德林这个次要角色并不是作品中可有可无的人物,相反,这个代表着社会生活中某一阶层、某类心态、某种命运的类型性典型,不仅展现了契诃夫小说的艺术造诣,也深化了全篇的主题。
在小说中,叶尔德林虽然只有四句话的正面描写,但却促成了奥楚蔑洛夫的两次“变色”,推动了情节的戏剧性变化。更主要的是,以叶尔德林的麻木愚钝、怯懦卑微反衬奥楚蔑洛夫式的官僚警察,不仅对人民大众颐指气使,而且对一切比他地位低、官阶小的人都官气十足。这不但强化了奥楚蔑洛夫性格的深刻性,更深化了对官僚警察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如果说奥楚蔑洛夫身上充分体现了奴性和官气的对立统一,那么叶尔德林三个动作和四句话表现的,只有奴性。他是警察却非官僚警察,经常出入达官贵人府宅,却永远只是逆来顺受的奴才和不会抗辩的听差。在奥楚蔑洛夫身边没尊严,在人民大众面前也无威风,他代表的正是底层“小人物”在那个时代的窘迫境遇。 小猎狗在文中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更是利用了一种最平常的动物进行描写。
1、平台作用:
契诃夫的《变色龙》描写的是警官奥楚蔑洛夫审理狗咬人的事。小说中的小猎狗无疑就是这起事件的肇事者。狗咬人算不上什么新闻,但作家正是通过这样一件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来表现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揭露沙俄专制统治下的警察制度的反动与虚伪。正是由于小猎狗的咬人,才给警官创造了一个审案的机会;才给警官的摇唇鼓舌,见风使舵,出尔反尔,趋炎附势,欺下媚上的丑陋卑劣的表演搭建了自我表现,自我暴露,自我塑造的平台;才将警官与社会底层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
2、导演作用:
《变色龙》独具匠心,巧妙至极的构思,与小猎狗这一角色的设置至关重要。警官审案,当时难以认定的是这一只小猎狗的身份,而周围的人也只能是拿不定的推测。也就是说对小猎狗的身份具有暂时不确定性。正是由于对小猎狗身份的反复推测,才造成了警官在审案时对小猎狗的观点和态度发生反复变化。如果小猎狗能够像鹦鹉学舌那样直接说出自己的主人来,即使警官具有魔术般的善变本领,那他无论如何也变色不成。妙就妙在这只小猎狗只会咬人而不能开口说话,它到底是谁家的狗,其身份只能由旁人去猜断。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小猎狗实际上是在借旁人之口舌在无声地导演着警官的变色“表演”。正是在小猎狗这位身份暂时不明的“导演”的导演下,小说的故事情节才得戏剧性的发展,警官的人物性格才得以层层展现,警官的变色龙形象才跃然纸上,历历在目,从而小说的主题才得以巧妙的揭示出来。
3、映衬作用:
在审案的过程中,一只小小的猎狗竟然使得身为警官的奥楚蔑洛夫忽时身冒虚汗,忽时又心生寒气。并非小猎狗具有神奇的特异生理功能,而是由于其身后蹲伏着一只更大的猎狗──席加洛夫将军。警官对于他们只有敬畏的份,只有死死地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对于这样一只小猎狗理所当然也只有加备保护了。罚狗欺了主的傻事,警官是断然不会枉为也不敢为之的。就这点而言,警官实际上就是一只奴性十足而又十分可怜的狗。再说,警官混迹于复杂而又混浊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为了求得生存的权利和空间,也不得不以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来换取苟且生存的一方空间。所以在审案过程中,他只得见“狗”行事,完全站在小猎狗的立场上为之辩护,替狗主持狗道,地地道道地成为了一只沙俄专制统治阶级豢养的忠实走狗。狗审狗案,狗狗相护,其结果当然是狗胜人败,不足为怪。警官和小猎狗分别担任狗案中的主审和被审的角色,共同表演了一场滑稽闹剧,可谓二狗同台,相映成趣。
变色龙讽刺了什么
第一,可以从人物自身的语言来分析。语言描写,指人物对话和独白。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应是他身份、经历、思想感情的反映。例如,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中,作者运用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刻画出警官奥楚蔑洛夫媚上欺下、狡诈多变、趋炎附势的卑劣形象。
第二,可以从人物自身的行动来分析。行动描写,指人物的行为、动作。作品中的人物是靠动作活起来的,人物的行为是受其思想意识支配的,因此,人物的行动反映着人物的思想和内心世界。例如,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写道:“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这个“摸”的动作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孔乙 己穷困潦倒的境地。
第三,可以从人物的外貌来分析。对人物外貌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物的性格或折射出人物的经历、命运。例如鲁迅的《故乡》中对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外貌描写,就反映了闰土性格和命运的变化,从而揭示出封建思想对人的毒害之深。
第四,可以从情节的发展来分析。所谓情节,就是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人物性格总是在情节的发展中逐步展现的。例如,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对主人公菲利普夫妇的塑造就是通过情节的展现来完成的。菲利普夫妇对于勒态度的前后不同变化,展现了他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本质,也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以及金钱至上的社会现实。
在小说《变色龙》中,作者契诃夫不动声色,不加议论,只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让人物自我表演,自我暴露,进行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冷峻无情的鞭答,具有鲜明的喜剧意味和强烈的讽刺效果。 一小说题目的讽刺。?
变色龙是晰蝎类的四脚爬虫,皮肤的颜色随着四周物体的颜色而改变,以防止其它动物对自己的侵害。作者以这种动物名称为题借喻讽刺小说主人公奥楚蔑洛夫,表现了主人公是一个见风使舵,媚上压下、反复无常、不知羞耻的沙皇忠实走狗。
这个题目本身就把讽刺的矛头对准了沙皇专制制度,无情地揭露了俄国警官制度的反动和虚伪、爪牙们的无耻和丑恶,批判了它反人民的实质。 二人物名字的讽刺 《变色龙》中的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和金银匠“赫留金”这两个姓名奇特可笑,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在俄语里,“奥楚蔑洛夫”有“发狂”“失去理性”的意思。
用这样一个姓名,使读者心中就产生一种“这个人精神失常”的感觉,可政府用一个失去理性的人来执法断案,岂不可笑!“赫留金”在俄语里是猪的“哼哼声、吐噜声”,这个名字,讽刺了小市民赫留金的粗鄙、庸俗,小狗咬了手指头,也想乘机捞一把,对长官曲意奉承,并以“兄弟当宪兵”作挡箭牌、护身。
扩展资料:
《变色龙》简介:
《变色龙》是俄国作家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契诃夫在该作中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虚伪逢迎、见风使舵的巡警奥楚蔑洛夫,当他以为小狗是普通人家的狗时,就扬言要弄死它并惩罚其主人。
当他听说狗主人是席加洛夫将军时,一会儿额头冒汗,一会儿又全是哆嗦。通过人物如同变色龙似的不断变化态度的细节描写,有力地嘲讽了沙皇专制制度下封建卫道士的卑躬屈膝的嘴脸。
百度百科-变色龙
本文来自作者[陈俊良]投稿,不代表史超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feischool.com/sch/6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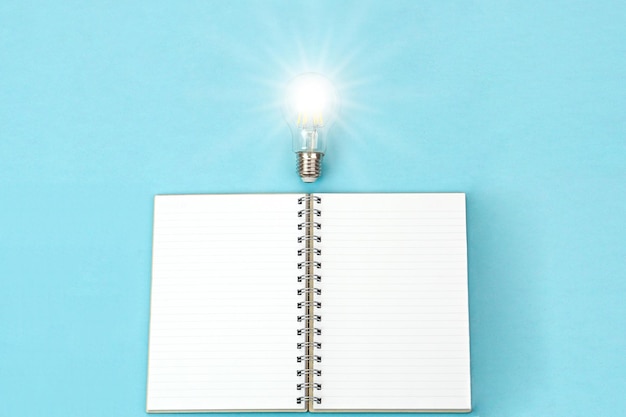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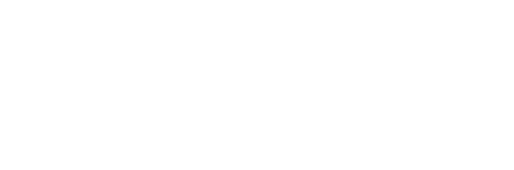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史超号的签约作者“陈俊良”
本文概览: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是对上诌媚,对下欺压。但他确要装出一副正义、公允的面孔,总想以美遮丑,因此往往丑态百出,令人发笑。契诃夫为了彻底剥下他的假面具,采用对比的方法,对他进行了...
文章不错《变色龙的人物介绍》内容很有帮助